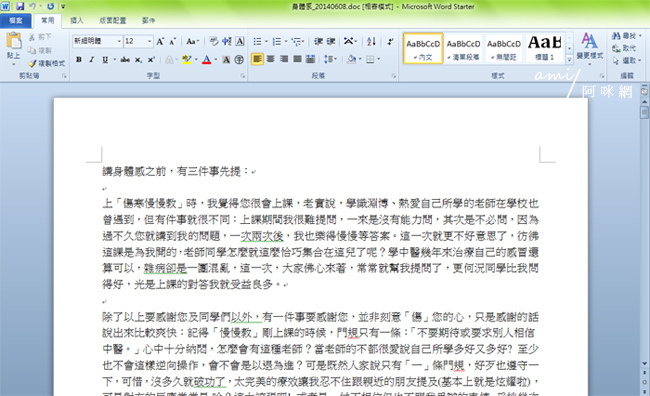
《圖片來自電腦截圖》
這是從叔叔古早的慢慢教時代到醫道課時代的一位學姐,
———文章開始———
講身體感之前,有三件事先提:
上「傷寒慢慢教」時,我覺得您很會上課,老實說,學識淵博、熱愛自己所學的老師在學校也曾遇到,但有件事就很不同:上課期間我很難提問,一來是沒有能力問,其次是不必問,因為過不久您就講到我的問題,一次兩次後,我也樂得慢慢等答案。這一次就更不好意思了,彷彿這課是為我開的,老師同學怎麼就這麼恰巧集合在這兒了呢?學中醫幾年來治療自己的感冒還算可以,雜病卻是一團混亂,這一次,大家佛心來著,常常就幫我提問了,更何況同學比我問得好,光是上課的對答我就受益良多。
除了以上要感謝您及同學們以外,有一件事要感謝您,並非刻意「傷」您的心,只是感謝的話說出來比較爽快:記得「慢慢教」剛上課的時候,門規只有一條:「不要期待或要求別人相信中醫。」心中十分納悶,怎麼會有這種老師?當老師的不都很愛說自己所學多好又多好? 至少也不會這樣逆向操作,會不會是以退為進?可是既然人家說只有「一」條門規,好歹也遵守一下,可惜,沒多久就破功了,太完美的療效讓我忍不住跟親近的朋友提及(基本上就是炫耀啦),可是對方的反應常常是:啥?這太誇張吧! 或者是一付不相信但也不跟我爭辯的表情。受挫幾次後,我就乖乖地退回這一條門規裏,平常也不愛讓人知道我在學中醫。
為了遵守這一條門規,我的病人就只能侷限在我及兩個小孩,原本以為這是一個限制,病人總是要看的多,才比較有經驗,不是嗎? 雖然您說學經方不必如此,可聽起來總覺得不太靠譜。幾年過去了,才發現,說不定這反而是進步的重要因素:不要去說服別人,就不必急於證明什麼,也不必「假裝」自己很厲害,(最近才發現,我以前很愛做這種事) 只關心有沒有對證,結果有沒有治好,對於療效也比較誠實,誠如舌尖上的中國的旁白:「家人的廚藝,毋須炫技」。此外,我和小孩可能是世界上最乖的病人了,我自己當然聽話,小孩子自然只能聽媽媽的話,讓媽媽照顧來按方服藥;也只有自已的小孩才能晾在那兒幾小時等媽媽把條文比對好才開出藥來,開錯了還能換藥,若是別人的小孩,父母大概會鐵青著臉說:「我們還是送醫院好了」。咱們仨一路摸索,現在,連我女兒對於自己生病的路數都有點感覺。初學時,我常苦惱於小孩表達不清,幾年下來,不知是因為訓練有素還是用藥有感,他們對身體感的描述相當生動而清楚。說起來,一般人無論是大人或小孩,似乎對於自己的身體感不甚清楚?
大概是2012年吧? 不斷地治感冒後,感冒漸漸少了,就想要好好處理一堆的雜病,(算調體質?) 吃來吃去的身體感不是打歪了就是力道不對,可是我不相信,這怎麼可能?以前治感冒多病一兩次就會知道怎麼醫,如今怎麼吃都怪,我不相信,一定是我程度不夠,於是更加地用功,吃更多的藥,經方的藥很少吃下去會無影無蹤,身體更覺得混亂,…,直到有一天,突然意識到:我這是在幹什麼呀? 我不期待別人相信中醫,自己卻落入中醫萬能的思維?於是我就將所有的藥停掉,離開中醫萬能的信念以後,我跟中醫的關係變得輕鬆了,很緩慢地有一搭沒一搭地試藥,同時也觀察自己有些是不是可以不要靠用藥,這樣的關係舒服極了。
這種體驗不知不覺也應用到日常生活上,當我不必去證明自己的時候,這種日子一來輕鬆,二來心思可以放在更有趣的事情上;此外,不必證明自己認知的「事實」,就可以把已知的事情一件一件杵在那兒,有衝突的事進來了,不必護著舊觀念,也不必急於接受新知,我不太清楚自己心裏怎麼處理的,但這些年來,有些觀念立馬就放棄,有些硬如巨石像的想法,居然如同冰淇淋般消失了。
漸漸地,我心裏也生出做到了才算數的感覺,莊子說「得於手而應於心」,的確有道理。現在,只要做不到的事情,就算跟別人的意見不一樣,也只敢小聲點兒說:可能是…。
上課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公平交易,但是這一條門規讓我算是大大地賺到了。人們常說:「不要錢的,往往最貴。」我卻常覺得:「人世間,最賺的往往不要錢,只是大家偏不要。」
第三件事小小覺得尷尬,是這樣的:關於莊子課,不只一次聽到別人說,”這個老師上課「真有趣」”,或是”那個JT呀,真敢講”,”內容「有意思」”。 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當然您上課時會有一些笑點,但是內容都很沉重,做起來都十分艱難。問您第一個問題的情境到現在還歷歷在目,當您淡淡地笑我:以妳現在的情況,做也是錯,不做也是錯。聽聞此言,直如五雷轟頂,記得在家傷心痛苦了一兩個禮拜。之後練習的艱苦也就不提了,每回我跟您討論都是被砍得遍體鱗傷,常常是趕快逃回家,慢慢地等傷口癒合。那別人的「真有趣」是怎麼回事? 他們是做起來很容易? 還是其實沒有實際在練? 我不好意思問,忍不住請教您,您認識練的人多,大家練起來是什麼感覺呢? 對了,我還曾遇見一種人,估計是聽過錄音檔或看過您的書,大力稱讚莊子課的內容很有道理,既然有道理不是該照做嗎? 的確是照做了,可是只挑部份來做,描述起來都是莊子課的道理,但怎麼聽怎麼怪。
這次我想請教的是身體感這件事,要講「感覺」這件事總覺得有點害羞,從小就把「感覺」畫上不好的成份,這是一種不理智、不可靠,甚至於是無理取鬧的代名詞,於是不論是講話或做事都要有憑有據,有邏輯、有頭腦、有思考,理智的人生才是正確的。我的確好像一直很怕被數落「不理智」、「無理取鬧」,這種隱憂成年以後看了許多電影就更加成形,在許多電影中,如果”壞人”要對男主角不利,就會設計陷害他成為殺人犯之類的,若是針對女主角,就會說她是神經病,把她關到精神病院。不知為何,總覺得精神病患比殺人犯無力感更重。(還是我比較同情女主角?) 回想起來生活上也是如此,如果被議論或責怪的是女人,那麼常有的罵人台詞是:「肖查某」(瘋女人),這話我從小常聽到,可沒什麼人會說「肖查甫」。
約莫過了三十年的「理智人生」,深以為然,直到前三、四年吧?我開始會「聽見」自己的講話內容,有好有壞,只是常常不能理解為何自己會講出那樣的話來;大概去年吧?我好像會「看見」自己行為,覺得討厭的就改掉,喜歡的就留著,有些只是自覺有趣:原來我是這樣的人呀? 次數多了以後,我有一種隱約的感覺,會不會自以為的「理智人生」並沒有這回事? 就單一的事情來說,我都可以講出一堆道理來,名曰:「師出有名」,然而從留意自己的行為到檢視過去的人生,我好像不是靠理智的頭腦在過日子? 其次,為什麼要用那麼多的道理來包裝自己的需要或行為?「想要」不就是最堅強的理由嗎?
既然討論的是身體感,所有的事情都沒有辦法講出「道理」來,都是「感覺」、「主觀感受」,也沒辦法套合書本上說的理論 (更何況,很多書我都沒看過),因此,也有許多感到困惑的地方。
從小,我對自己的身體多所怨懟,其一是生病老是治不好;其二,有幾次當我要展開偉大的前程時,就會生大病,努力地展翅高飛,卻被一棍打在地上,好痛;其三,偶爾就會出現「怪」行為,別說旁人無法理(諒)解,就連我本人也無法了解為何要這麼做。於是,我把所有無法用主觀意識可以解釋的部份,姑且稱之為「身體感」
第一、二項自從上了中醫、莊子課後,了解問題所在,未必能完全解決,倒也不困擾了。第三項似乎可用您說的「後味」來解釋:某些人大家都說好,我也覺得好,可有些公認的好人我卻不喜歡;有人對我溫柔體貼,相當受用,有些人的安慰只讓我覺得渾身不舒服;我以為我喜歡有正義感、努力負責的人,可是對於某些很「壞」的人,卻是討厭不起來;我極討驗大男人主義,可是我到南部讀書時,卻頗享受某些「大男人」;有些人對我直言不諱,聽了就刺耳,有些忠言雖然逆耳,卻願意好好反省;就連同一個人,原本相處不錯,後來不知為何卻成了雞肋;做事情該有條理、有計畫,然而我常也會有脫軌的演出。
諸如此類的人或事情,一件一件翻開來看,漸漸讓我覺得自己的運作系統其實很混亂,檢視久了,發現其實都是自己主觀的感覺,出問題的部份常常是在我想用理智克服自己的主觀感受,克服不了的,自己就崩潰了。比如說,我其實一點也不喜歡我小姑,若不是因為親戚關係,這樣的女生不太可能踏進我的生活,其實,我小姑在世俗眼中是很好的好人,這我完全同意,可我就不喜歡她,反而我喜歡她兩個女兒,於是我就開始自我說服,於是做了許多「勾引」的動作,當然小姑也不是能辨認的人,一般人難以做到吧﹖「人家對我這麼好,一定是愛我的,不是嗎﹖」於是她就上勾了,等到我狠心地決定其實我不愛她,事情就變得有點慘烈。又比如說,當年傻傻地聽大家建議去讀專科學校,最後覺得自己還是想讀大學,更傻的是居然跟流行去準備考技術學院,(其實,還有更傻的是去補習,究竟為何讀書需要補習呢?)當我傻傻地來到北部的這所技術學院,當場崩潰,怎麼辦?怎麼辦?這一年來的苦讀、家中經濟的困窘、一大家族的不諒解…,都無法讓我妥協去讀這所學校,回家後又生病又傷心了大半年,最後還是狠下心來準備想唸的大學,剩下的事情就簡單了。
像這樣的事情過去相當程度地困擾我,大部份的人好像也可以不管自己的感覺和小姑過得很好,也能既然準備了就去考嘛!考上了就讀嘛!奇怪,人家是如何做到的呢?我卻老是拗不過自己的身體感,每次兩邊作對起來都很受傷。(對了,說不定,以前那些醫師說我壓力大,可能也是有道理,我常常要那麼努力與自己的身體對抗,是非緊張不可的。) 這些年來漸漸地接受自己的身體感,卻也會有小小的困擾產生,對某些事情、某些人,就只是覺得怪,但完全說不出「道理」來,所以也沒辦法跟旁人說什麼,也無法解釋什麼,估計說出來會被認為是神經病,得等到事情反撲回來才能了解原來怪在此處,可我分不清,這是我的身體感清楚呢? 還是我自以為怪,就運用了心想事成法呢? 而且我以前還會有一種壞習慣,當身體感覺到「不自然」時,只通知了「怪」這個訊息,我根本不知道是為什麼,可是這種不知道很不安,就安插一個「罪名」給對方,比如說,有人送禮來,我高興地接受了,另外有人給我禮物我卻不大想收,總之,怪怪的,我就會開始自我解釋:對方可能對我有所圖謀啦…。現在我比較克制了,比如說最近我們到別的機構參觀,從頭到尾我就覺得那個接待的人怪,但不敢再隨意安插罪名給人家,後來遇到跟對方熟的人,忍不住問了,對方告訴我一個故事,我才恍然大悟。這些覺得怪的事情,有些甚至於會引起情緒,或一再地心煩,需要一再求證,然而,常常不會幸運地知道答案,就像是看懸疑推理劇,但是一直看不到大結局是什麼,可我好想看結局,不知道要怎麼做才能看得到?
這一次您花了不少時間在講心想事成,我心中有點納悶,這個需要花很大的力氣練嗎? 記得跟您提過,當我親眼看到您親自示範「心想事成」這件事後,我在心中想著:嗯! 就這樣? 那我也會。之後日常生活各式各樣的「預感」或「神通」變得很平常,就連「詛咒」別人也做得到(您說是「預言」?) 但話說回來,卻有兩點是我不太想得清楚,其一,我並沒有做什麼「動作」,通常只是心中只是淡淡地想著我想要怎樣怎樣,那件事就會成真,甚至於當我對某事感到困擾,大宇宙就幫我提出解決方案,方便又實用。其二,有一回遇到了一個好運氣,對方很驚奇,我只是淡淡地笑說,想要什麼自然會得到什麼呀! 她楞了一下,回問我,那你為何不求中樂透呢? 對喔,為什麼我不要求中樂透、住帝寶呢? (莊子課也提到的) 想了一陣子以後,我猜可能是每當我想做什麼事時,做那件事的錢就會來,只是不知用什麼方式來而已,換言之,若是「真心」想做一件事需要2億,就會得到2億,沒事就得到2億,會不會覺得要照顧它們而感到辛苦? 還是說,我根本不相信能要求這麼多?
心想事成很愉快又很好拿來說嘴,說也奇怪,雖然我覺得不難,但似乎也不特想要更加的精進,姑且猜一猜,我淺薄的人生能接觸到的所謂的修練幾乎都強調現實人生的「報酬」,從處理情緒問題到信仰,現實人生看到的都是最後如何的成功,相反地,另一邊的人卻是乾脆要大家摒棄所有物質與虛名,這兩種都聽起來有道理,但兩種都不舒服,不管我依靠那一邊,總覺得怪怪的,也有一點另一邊似乎比較好的感覺;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這兩種人都令我感到不舒服,那種完全放棄物質人生的長輩,苛剋得不得了,本人看起來就像棄婦;至於虔誠求神的人,例如我家族裏一大堆的長輩,神佛並沒有賜予他們富足美滿的生活;到了都市生活後,不乏有些人會說他們的成功是因為某種信仰或是心靈修養,我也不敢說是假的,就是覺得怪,有一種不懷好意的猜測,那些人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的秘訣是什麼,反正有「成功」的事實,怎麼解釋都行,好比說,我們從細胞中可拆解出醣、水、蛋白質、核酸…,難道說就可以將這些組成一個活細胞?那麼我們把一個範本拆解行為特質,再把這些特質組合起來就能複製出那個人的「成功」?。
莊子最奇怪,幾乎都沒有給我們一個保證說,只要學會這一套心法,就可以….。
第二次莊子課聽說了零極限,看了書也感到納悶,這樣的動作跟我媽媽拜媽祖、拜公媽有差嗎? 那為何人家可以練就那樣的法力,而我的長輩們卻一直生活不順遂呢?至於我本人,聽起來很簡單的事呀,可練來練去不成名堂,安慰自己沒慧根就放棄了。後來,我發現練莊子跟練夏威夷大法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後者沒有身體感。記得我跟您提過,原本練習不辯論是咬著牙的,後來能大幅降低辯論次數,是每當話一說出去會有撞牆感,同一個人常會給我撞牆感就知道避之為妙。諸如「責任感」(不是一般人說的那種責任感)、「事有先後」(或說順序感)、「謙虛」、「看到自己的行為」、「黑暗面」…,並不是我知道了這些事,而是感覺到了,再弄成語言講出來。比如說,我並不是認定辯論不好,而是說:「對不起,我弄錯了。」又順口又舒服,「應該是…,可是….,一定是…」這種理直氣壯的話,不愉快。說起來,練莊子跟吃中藥的身體感有點類似,最主軸的感覺是變輕變鬆了。
可是這些練莊子的身體感能帶來什麼「好處」呢?嚴格來說,沒有耶。
此外,直接練心想事成好像會有點問題,我覺得—只是隱約覺得,這個順序有點怪怪的,主觀的我要東要西也能得到,可是大宇宙賞給我的好像比我自己想的更好,(到這兒,有點覺得自己表達能力不足了),好像是說,如果這一生是來造一架能到月球的旅行機,那麼大宇宙給我一套綜合方案比東要一個零件、西要一個工具來得好。或者說,與其我想要什麼,不如說我想知道「身體」想要什麼,身體想要的比較是真心﹖還是說違抗不了身體感﹖抱歉,語無倫次了,容我再想想。
這一次上課有一個特別的部份,即時間感,以前我對空間感比較明顯,常覺得這個世界不是如我想的,有點不真實。和別人面對面講話,明明處在同一空間,卻覺得完全不同一個世界。上回您要我們殺三個人,我的經驗與那位有時間感的同學有點像,(我就說嘛,同學們比較會問問題):有一個鄰居一直困擾著我們,任由養的狗到馬路大便,而我家剛好就在旁邊,因此出門都要小心走路,爭執過後發現無效後,我就開始想這件事到底是為何具像化到我面前,雖然知道生氣沒用,但是一直無法解決,出門仍需小心。直到三月底,您建議我們「殺」三個人,在這之前我已經殺人無數了,一時不知要殺誰,可既然老師給作業了,好吧,就再殺這個鄰居及辦公室打掃的歐巴桑,沒幾天,隔壁就貼出搬移啟示(他們家是開店的)。我只是不解,鄰居的困擾已有好一陣子了,為何以前殺不成,這次卻立馬見效呢? 至於殺不成打掃的歐巴桑的問題我還在想。
關於「殺人」這件事,同學們的回答—包括我自己—都是某人讓我們困擾,於是我們要創造一個沒有對方存在的實相,當然啦,老師的題目是要「殺人」嘛。之前我的確是殺人無數,情況卻略有不同,比較多的經驗是,反省的結果通常是我對不起人家,對方的生命沒有我其實比較好,就別再打擾人家了。無論是殺別人,或是幫別人殺了自己,身體感都很好,奇怪,以前我是在過怎樣的人生呀﹖
以下講講學中醫的身體感:
大家常說,有病就要「治療」,甚至於說「提早發現,盡早治療」,然而學了中醫之後感到很困惑,從吃麻附辛開始,我吃藥從來沒有「治療感」,特別是「退」燒這件事,吃西藥的身體感的確是「退燒」,(退是動詞) 無論是我本人或小孩,都是這種感覺,反之,吃中藥從來沒有「退燒」的感覺,只是「不燒了」,我自己一直是清清楚楚的,後來,有一次给小孩用了小健中湯,高燒沒了,意識到不是退燒,那種身體感用中文的「和」或許比較接近。我自己吃溫經湯前,是活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日復一日熱烘烘地,用藥以後,彷彿換了一個場景:綠草如茵、大樹成蔭、涼風徐徐吹來。估計若是吃西藥的身體感大約會是一盆水直接潑熄了火,然後冒出濃煙…。
於是溫度計上客觀的數字對我來說變得很虛幻。有一回,婆婆問我小孩發燒幾度,答曰不知道,沒有溫度計。老人家甚為不悅:沒有溫度計,怎知道發燒了沒,發燒到幾度呢? 剎時之間我也被問傻了,對呀,的確是不知道幾度。事後檢視這件事,我想,不但不需要知道幾度,知道了更為難,小孩發燒了一看便知,相對於溫度,臉色如何,那個部位在燒,或者我抱著小孩時自己會不會跟著燒起來更重要。
(題外話,當初我生小孩並非自己想生,夫家堅持要有小孩,而我當時不敢離婚,就生了。原來覺得是苦差事,沒想到小孩子真的是寶貝耶!他們提供了「身體」這種東西,我相當享受給小孩餵奶、洗澡、抱抱、在床上滾來滾去或玩熱狗遊戲;與其他人相處再怎麼輕鬆也比不上跟自己小孩在一起來得自在,我們家最嚴肅的討論類型大約是,有一回我們四人很認真坐在客廳中,討論在上課中如果想放屁,要不要舉手跟老師說讓我出去一下?在辦公室要不要出去放屁? 小孩漸漸長大,四面八方湧過來的要求,諸如功課、教養、健康…,都不是有趣的事。)
有一回隔壁桌的同事看我在吃藥,問了我一個大哉問的問題:「妳吃中藥,如何知道是好了,還是就症狀治療而已?」一時之間我就被問倒了,對喔,完全無法證明呀。不久,用藥的經驗多了,就明白嘞,當然是好了,而不是症狀治療。這完全無法用數字證明的事情,身體卻是清楚無比,細微的身體感不說,最明顯的感覺是身體變輕了,也有一種清爽的感覺,我不記得曾吃過西藥有身體變輕的感覺,說起來吃西藥的身體感比較像是在「治療」,有一回聽一位感染科醫師介紹抗生素殺菌的原理,主要有三個途徑,一是細菌身上有一個鎖孔,抗生素帶著鑰匙去鎖起來,其二,帶著針筒將毒液注入病菌中,最後是遍灑硫酸把細菌燙死之類的。以前用過抗生素,主症狀雖然會減輕,總有這裡那裡不爽快感,這還滿合理的,很有「治療感」。
說起來吃中藥的身體感比較像是調整了身體的「什麼」,以致於原來生那個病的「條件」消失了,所以就不病了。說也奇怪,意識到這件事以後,我好像對於生病比較沒有敵意了,一般人不喜歡提到疾病或死的字眼,我現在聽到到都沒有不舒服感。聽到別人生病了,跟出國幾天差不多的感覺,至於我本人生病,身體上當然不舒服,但偶爾也會出現「只是不速之客到我家來逛逛」的感覺。至於預防生病的事我都不太做,也不會叫小孩做,不是我很漂ノ,只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想生病自己就能生一個,不需要別人傳染給我,不需要生病時,旁人的病菌大概也不喜歡跳到我身上來吧?
原本吃藥就是把病醫好而已,大概是從小柴胡湯開始吧?原本是要處理某些狀況,用藥之後不但症狀不見了,連帶某種情緒也會消失,到了烏梅丸更加明顯,後來發現,如果能意識到某個情緒要起來了,就在那0.001秒內,來得及在心中唸出:嗯,這是大瀉心湯證呀(或抑肝散、小柴胡湯…),那個情緒就會化去了。第一次問您,答曰的確用了烏梅丸可能修補到肝經,有可能平撫情緒,當時我隱約覺得,藥能醫,那麼有沒有可能練莊子也行? 上回再度跟您提到這個情況,您說道女生的確是可以做到這個事情的,那不禁會想到您講到小方或丁助教,他們是因為與大宇宙感情好,或者是表面意識鬆所以能自我療癒,還是說其實是因為他們會治這個病?吃過這個藥,就會有身體感,只要通知身體是那一種證,未必需要真的吃藥就會好? 那一次講到小方不需要吃麻附辛也能自癒,這讓我感到相當困惑,我也是麻附辛的老病號了,回家查了自己寫的病歷,發現已有一年多未吃麻附辛湯了,奇怪,明明我還記得不久前都還會喉嚨痛,咋沒吃藥呢? 會不會習慣成自然? 一旦有證我就在心中默唸:麻附辛湯、麻附辛湯。不痛自然就不必吃藥了。 上週吧? 我突然感到背痛,落枕問題也是困擾多年了,一旦痛起來,連轉個頭都很困難,西醫給鎮定劑肌肉鬆弛劑加物理治療,中醫就做針灸推拿,沒有一週以上不能搞好,弄了一個月的都有,不過,他們倒是異口同聲說我壓力大。後來是吃通脈四逆湯好的,這一次當背痛時,開始心中默唸:這是通脈四逆湯證,通脈四逆湯、通脈四逆湯…。於是症狀就停在那一刻,之後兩三天有再好一些,只是有點不耐煩,還是吃了1g的科中,就好了。至於舌瘡,(輔行訣)大瀉心湯的咒語更有效,隔天就好了。寫到這兒才想到,既然吃真武湯把水擠出來,為何沒想到用念力排掉呢﹖
上次李辛老師來上課,老實說,那樣莫測高深的學問不是我接收得了的,但是課後著實是「安心了」,課堂中不斷在心中點頭:對對對,吃這個藥就是這種感覺。在此,也冒眛請教您,我覺得您隨後上課也會多講服藥後的身體感覺,是我的錯覺?還是您的確是刻意這麼做了呢?
說起來,生活中成就一件原本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對於破解既有的價值觀頗有幫助,例如學中醫,世界上居然有這種我無法想像的醫學存在,更奇怪的是,又不是沒聽說過,街頭巷尾也到處有中藥店呀,怎麼在同一個空間卻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於是,聽到再離奇的事情也就不會急著去否定,我原來有的信念結構,除非是我意識不到,否則都不敢認定這就是事實。比較難的部份是,不知道自己原來是被某種信念圈住了,就像「罔兩問景」這個故事就覺得滿黑暗的。
之前偶而會跟朋友聊起吃東西的身體感,是我太敏感還是大家不太重視這事? 之前台灣出了幾件食品安全的問題,諸如塑化劑、麵包、醬油之類的,發生這些事我並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台灣人大驚小怪的反應,那樣整齊劃一的口味,那麼鬆的麵包,詭異的「黑」色醬油,從來不覺得怪嗎?聽到這些消息不是應該露出「原來如此」「難怪呀」的表情嗎? 倒是這次上課講到味精污名化的問題,有點驚訝,咦?味精吃了會口渴不是嗎?可是人家大陸人卻沒事,同學也說,我們小時候也用味精呀,仔細想想,至少我國中以後媽媽煮菜是會用味精的,當時的確沒有那種永無止盡的口渴感,那麼凶手不是味精?還是說現在的味精跟過去不一樣?下次有空買一包來吞看看。順便,也說個小趣事,之前您提到香煙污名化的問題,奇怪,我明明覺得煙很臭呀,許多抽煙的人一踏進房間,一股臭煙味就先飄進來了。您又說自己和陳助教煙抽得很兇,可是當我和您或陳助教站得那麼近,卻不太覺得有煙味,這是怎麼回事呢?於是我就到便利商店隨機買了幾種煙,點來聞聞看、抽抽看,嗯,香煙不是一種臭的味道,所以我想這可能跟抽的人有關吧? 過濾器有問題,經過的水或空氣大概就有問題吧。
題外話,日前有一個孩子到捷運上隨機砍人,看到新聞,也回憶起我曾經也有過這種感覺,很煩很不高興,很想衝出去把所有人都砍死,會夢到我將一堆人排好,一一將他們射死,追殺別人或被別人殺害….。可是好奇怪,記憶所及完全不曾再有這樣的感覺,若不是這一起事件,我根本就忘了有這回事,這種感覺究竟是如何消失的呢? 更重要的是為何有如此強烈的情緒呢?
———文章結束———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